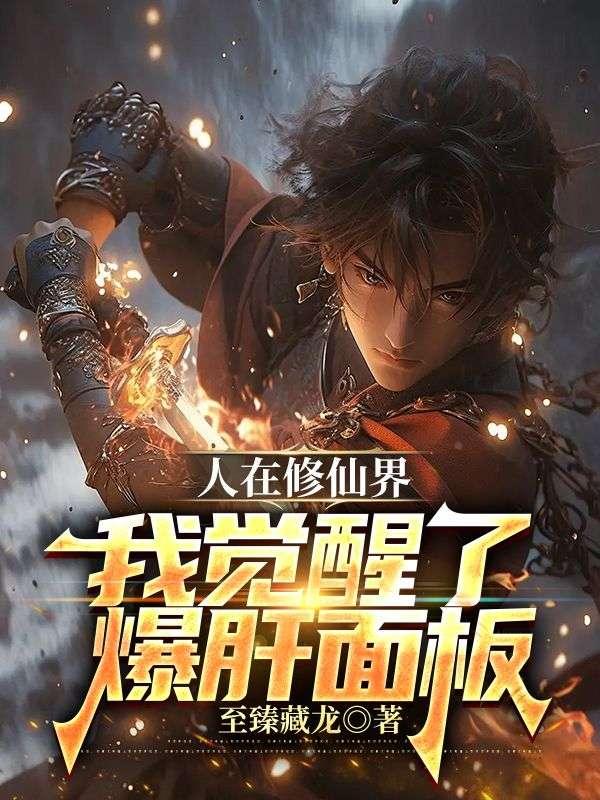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将门by > 第19章 ☆梦见了玄女娘娘☆(第4页)
第19章 ☆梦见了玄女娘娘☆(第4页)
雪砚安静地把梦境品来品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相较于混乱、喧嚣的梦境,这婚房中的气息真叫她心旷神怡。
闻上去,就像是幸福本身。
她微微仰起头,目光瞧住了一旁的夫君。
他被稀薄的光线勾勒在那里,沉静,冷峻,呈现着一种极致雄性、阳刚的好看。
雪砚怔怔地望了一会。因为听不见他的气息,忽然又有些莫名其妙的害怕。想到梦里的大棺材,她的心怦怦直跳,石块一样夯在了心壁上。
她忍不住把手伸过去,悄悄放在了他的鼻端。
竟然感觉不到任何鼻风。
雪砚吓得脑子里一烘。忽然,她的手被他张嘴叼住了,那喉咙里发出猛兽一般凶残的呜咽声。好像逮住了一只好吃的。
她笑起来,轻声抱怨道:“你睡觉咋没声儿,吓死我了。”
他松开嘴,无奈地说:“你这胆小鬼真是没救了。为夫只是在入定,莫怕。”
“哦。睡觉时入定么?”
“嗯,练武养成的习惯。”他长长地匀一口气,慵懒地伸一伸腿,问道,“方才睡得好好的,你哈什么?”
雪砚愣了一下,才说:“我没有哈什么。”
周魁“嗯”了一声。没再刨根问底。只是微调一下睡姿,试图拉开两人间的距离,让这场觉睡得更“素净”些(因为每到凌晨,他会特别想)。
雪砚歪在枕上,一时沉默着。
梦的头绪有点乱,有点荒谬无稽的。仿佛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神游。而且,老祖母的遭遇跟上一次也存在矛盾。
她要是对他说了,只怕自己的话就显得不大可信了。
还有关于儿子的谶语。事情关系周家几百口人的脑袋,绝不能随便就这样从她嘴里问世。必须弄个确凿,慎之又慎才行的啊。。。。。。
雪砚辨认着黑暗的浓度,轻着声气儿问:“啥时辰了?”
“马上寅时。”
“诶,你为何总能一下就知道时辰?”她又悄悄地好奇,“你这人咋这么厉害?”
周魁心里发笑,别人家的女人是不是也这样?喜欢夜里各种花样地作祟,有时真像个孩子。要是正经搭理了她,马上会有一堆的怪问题追着你不放。
他闭着眼,不正经地应道:“因为四哥是更漏转世,专给你报时的。”
雪砚笑了。
视线穿过幽暗,凝望着他模糊的轮廓。
半晌,用轻纱般的声音说:“四哥,我真想给你生个儿子。”她这样说着,脸上臊得滚烫。
周魁掀开眼帘,嘴角微微地翘起了。不经意间,又被这家伙甜得心里稀巴烂。
她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若是带兵,必是一个善于奇袭的猛将。
过一会,他才揶揄说:“生儿子挺废腰子,你能行么?”
她弯了眼,“我以后多吃一点,每顿两大碗。”
周魁笑了一声,“果真如此才好。为夫倒有福了。”
他的手在她身上拍了拍。把她当个孩子似的。
雪砚自认并不像个孩子。她自认为身和心早熟透了。只是这样一种无邪的怜爱却是她最贪恋的,远胜于另一种狂风暴雨的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