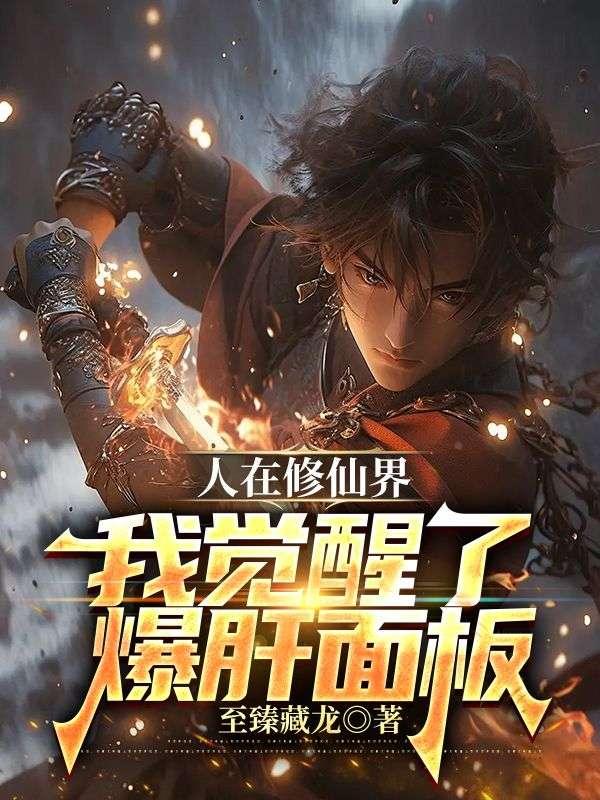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神女与青狮结局 > 280290(第12页)
280290(第12页)
长晔没有半分回避地与她对视,心中不由得想到了从前,难怪彤华有那般的读心天赋,难怪彤华能有足以连杀十一神那么强大的力量,难怪她最后那么着急,生怕自己做不完这一切,生怕他不肯答应……
原来是因为阿玄啊。
彤华要为陵游报仇,自知余力不足,不惜自绝也要唤醒阿玄的神智,以夺取她的力量成事。但彤华想要毁灭,阿玄想要顺从,她们的意志从根本背道而驰。
彤华压制不住阿玄,就只能望他快些,但他们还是没能来得及。
在阿玄到来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完,此刻对坐面前,还被她直白地戳穿了一切。
那么他也就没有什么遮掩心迹、缓加试探的必要了。
“弊端?”
长晔冷笑道:“阁下既然观世所知一切,应当看到过天机楼内是什么样子罢?神魔视凡人如草芥蝼蚁,他们的一生经历,落笔不过一卷命书,尽是天道早已定好,任他们如何挣扎、不肯听天由命,也不过如此而已。我等神魔,又与之何异?”
他目光泛出一种不甘又生厌的冷意,道:“天机楼没有我们的命书,那我们的命书又置于何处?新境若是高于此世,是否得见我等命书?阁下来自新境,可见过自己的命书?”
阿玄面无表情道:“既是世间生灵,自然遵循天道规则,若跳脱于命书以外,生祸只在早晚之间。你本是天生神明,若无意外,寿数本可与天同齐,若此世崩塌,你已无生路可选。又何必如此?”
长晔道:“若我偏不愿意呢?”
他嗤笑道:“与天同寿,天道可问过我的意愿吗?这样蛮横又霸道的天道,我为何非要听命顺从于它呢?”
阿玄望着他,道:“一旦世界运行的轨道发生重大偏移,而命书已经无力修复扭转的时候,命轨便会现世作以纠正。你是故意挑起战争延续许久,想要引出命轨,设法打开命轨通路……”
她声音放缓,一字一定,道:“从而毁灭天道禁锢,回溯至创始之初,从头来过。”
长晔轻笑一声,道:“妙临叛离天界之前千方百计封锁天机楼,不就是意味着,命轨已在天机楼之内显露原形了吗?我离回溯,不过一步之遥罢了。”
阿玄道:“只这一步,你已走了数千年了,可有办法将她从地界带回来吗?”
长晔听见这话,问道:“阁下总不至于是见我束手无策,故而特地出现帮我的罢?”
阿玄道:“我永远也不会帮一个妄想毁世的无理之神。”
长晔道:“你若想要偏帮长暝,以期维护此世稳定,那方才就不会站在天界这边了。”
阿玄道:“我对偏帮毫无兴趣。不帮你们,是因为你们欲图毁世,不帮他们,是因为他们满口谎言,更非善类。”
长晔闻言便笑道:“如此岂不正好?既然两边都不偏帮,阁下何必还要在此处多言,速返新境去罢!”
说完这话,长晔便看到对面始终沉默不言的玄沧抬头剜了他一眼。
阿玄没有接这句话,只是与他道:“我从未见谁可以干扰命轨运行,又何况是打开命轨通路?命轨运行的规则亦是天道既定,若是天道毁灭,命轨要如何保证运行?回溯一事,只是传言,当不得真。”
长晔道:“真与不真,我要试过才知道。”
阿玄道:“若你只是为了复活霜序,自然有其他办法。”
此言一出,玄沧下意识看向长晔,身体也向前微微倾了倾,生怕长晔因此而做出什么来。而阿玄恍若未觉般继续道:“如今定世洲的那位神主,也是前任献祭换回来的。只要你们的禁咒解除,二代神魔全部自本体之中苏醒,那么让她完全复生,也并不艰难。”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谈判。谈判,要有未知,要有试探,要一步一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阿玄对他们的底线与所想全然知晓,他们近乎于完全透明地暴露在谈判桌上,这绝不是什么谈判该有的样子。
可在这一刻,长晔心中对她的那些戒备和警醒却突然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
“我不只是为了霜序。”
他爱慕霜序,为了霜序做过许多事,在霜序死后很多年里,他都一直在寻找让她归来的办法。那年彤华因为步孚尹受刑,文宜闯到上天庭,他明知道那是彤华故意为之,却仍旧愿意为了文宜体内那缕深藏的霜序的灵识而答允之后与彤华的合作。
文宜在定世洲也要照管部分事务,如与他有关,他便处处为她让步。他想什么姊妹情深,彤华说得好听,到了真为自己牟利的时候,不还是将文宜推出来吗?
文宜此世性情单纯,他得先护住了文宜,才有办法设法复生霜序。
诚然如她所言,如果想要复生霜序,他不止有一个办法可以尝试。只要是为了她能回来,他什么办法都愿意尝试。
但他不只是为了霜序。
牢笼里的囚徒是不能见到自由的。一旦见过了自由,他们就会对逼仄而受控的现状生出不满,有不满便有二意。他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群高高在上的神魔,享受着掌控着这整个世界的权利,那也许除了遗憾以外,也就只剩下些虚情假意的懊悔。
可偏偏这天外有天,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这世间的一切,却原来万事万物尽皆平等,尽为天道掌控之下的牢笼囚徒而已。
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囚徒,也从来不肯甘为囚徒。若是天道执意如此,那他们豁出命去又如何?
这新境的神女,为了让他们甘于现状、顺从天意,妄图用所谓的男女之爱来捆绑住他,让他从此俯首为囚,何其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