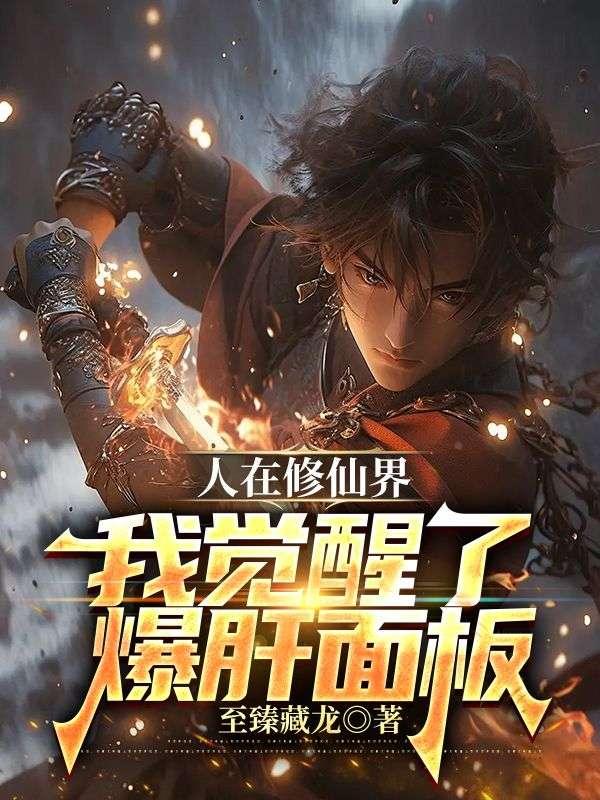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透骨香图片 > 第六卷 乌雀翎60哀求高高放人失败联合医院6p (第9页)
第六卷 乌雀翎60哀求高高放人失败联合医院6p (第9页)
夏知被操得脑袋一下下顶在柔软的枕头上,两条腿被拉成一字马,粗大的东西破开软嫩的穴肉,重重地沉进他娇小的肚子里,沉甸甸的两个大囊袋把少年白嫩幼小的阴部打得通红。
宴无危眨眨眼,“全吃进去啦。”
……
一夜几个人轮流,把那小小的花腔射得鼓鼓囊囊,少年小肚皮被射得仿佛怀胎六月。
前三个人的时候还有力气哭闹尖叫,踢蹬骂人。
贺澜生拍拍屁股,瞧着被操开淌水的穴,“宝宝像在吃奶呢。”
他抹了一些夹不住的又塞进去,调笑,“我这还等着喂宝宝呢,宝宝多吃点。”
夏知瘫软在顾斯闲怀里,两只鸽乳已经被男人轮流玩肿了,乳尖更是从樱桃变成了栗子,下面被捅得熟红,又热又痛。
他大概想骂滚,但张张嘴,黏稠的乳白的液体就从嘴角流淌下来,舌尖,牙齿,喉咙里,上颚,全部都是。
最后又侧开脸,扑簌簌流了眼泪。
后来就被肏得只能被人吊着发软的腿,露着屁股夹着男人的大肉棒吃奶了。
顾斯闲掐起他的下巴,亲亲他被汗湿的额头,“宝宝……哭什么?”
他低下头,与他抵着额头,声音柔和问:“后悔了吗。”
——后悔什么?
夏知张着嘴,舌尖卷着麻木的香气,眼瞳被泪水浸透,整个世界都模糊了。
后悔用朱雀戒逃走?后悔欺骗高颂寒去西藏?后悔从戚忘风那里骗药?后悔上了宴无危的贼船?后悔没有答应高颂寒的追求?后悔当初从顾宅联合顾雪纯逃跑?还是后悔……
顾斯闲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贺澜生重重捅了进来。
夏知直直地绷起了身体。全天。出文]机器人1103796821
他浑浑噩噩地细数自己潦草的半生,只觉此时此景,顾斯闲这话问得让他浑身都疼,比被五个人轮流操都疼。
他懦弱不堪地逃避过,也勇往直前的坚韧过,哭过,笑过,恐惧过,也曾经爱过,夏知的一生是由夏知自己构成的,或错或对,向着自由的终点,他从不后悔过他做出的任何选择。
唯一后悔的,就是那个蝉鸣风静的夏天。
他不该偷吃那颗献给神明的供果。
……
沾满了香味的湿透床单被人换过好几遍,到后面几个人一起,夏知已经没有力气哭闹了,他也不知道操自己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又到了谁的怀里,有时候浑噩叫错了,也会挨打,白嫩的屁股本来就被结实的腰胯撞肿了,这么一打更是雪上加霜,疼痛让夏知稍微清醒了一点点,抽噎着叫对了——“哥哥!!”
他的嗓子嘶哑带着可怜的哭腔,"哥哥别打了,好疼……”
于是那个凶狠的男人好像便有了疼惜他的意思,带着疤痕的大手揉着他火辣辣的屁股,背贴他把他抱住,他好像说了什么,又似乎没有,这份在苦难中令人依赖的点点温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夏知就听到了宴无危含笑的声音——
“夏哥偷懒啦!腿又偷偷夹上了……好不乖,要掰开哦。”
夏知立刻发起抖来,他嗓子哑了,已经叫不出声了,他只能在内心歇斯底里的重复着不要,被击溃的身心前所未有的依赖着身后人的一点点可怜的温情,他用力夹紧腿,脆弱的眼泪汹涌而出——不要,戚忘风,不要……
身后的人顿了顿,随后他的大腿就被一双大手缓缓,但不容置喙地掰开了。
那一刻。
那片被现实残忍击碎捣出软热懦烂渴望倚靠的血肉,再次失去了倚靠。
它只能独立瑟瑟在冬日冰冷的浓雾中,又被寒风锤炼成坚不可摧的冻铁,锤削不烂的顽石。
“哈哈哈哈。"他听见宴无危孩子般悦耳的笑,他凑过来,靠在他的耳边,嘻嘻笑说:“夏哥,我要进来啦。”
无尽的痛苦中,夏知发着抖,听见宴无危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夏哥不爱小狗。”
“也不许爱别人哦。”
……
天明了又暗,暗了又明,这一夜漫长地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