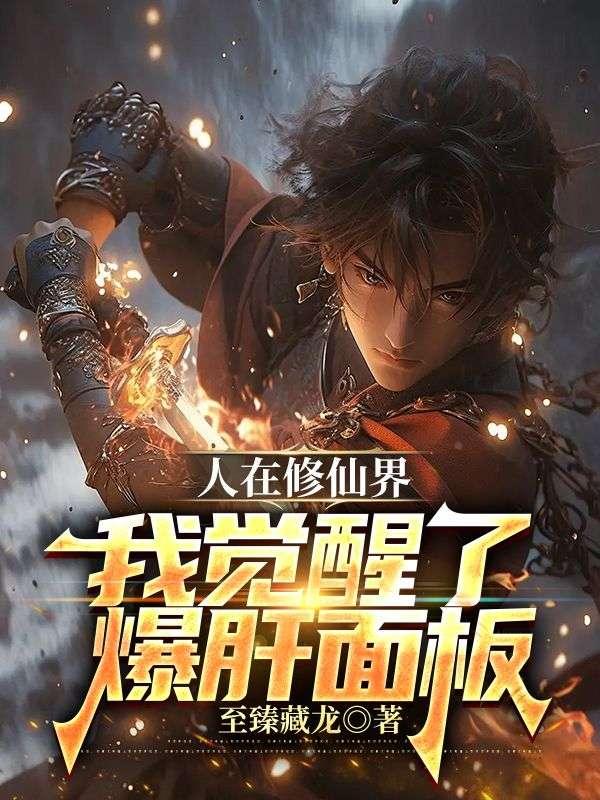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名利场这本书怎么样 > 第十四章 克劳利小姐在家(第1页)
第十四章 克劳利小姐在家(第1页)
第十四章克劳利小姐在家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辆旅行马车正朝公园路某座极其舒适、家具齐全的房子驶去,它的车身镶着菱形纹章,厢外后座坐着个阴着脸的女人,她戴着绿面纱,留着长卷发,主人的亲信,一个大个子男人坐在驭者座上。原来我们的朋友克劳利小姐家的马车从汉普郡回来了。马车窗是关着的,那条平常爱把脑袋或者舌头伸出窗外的西班牙肥猎犬,现在正趴在那阴着脸的女人大腿上休息。车停下后,好几个用人从马车里移出了一大捆披肩,有个一路陪同这捆披肩的姑娘也在帮着挪。原来里面裹着的是克劳利小姐。下车后,她随即被送上楼,又被扶到事先已按病人规格暖好的房间和**。跑腿的出去把她的大夫们找来。他们来了,问诊、开药,又走了。走之前,陪在克劳利小姐身边的姑娘听了他们的意见,然后给克劳利小姐服用了各位名医开的消炎药。
第二天,近卫骑兵团的克劳利上尉从骑士桥军营骑马赶来。他的黑马拴在他生病的姑妈门前刨草堆。他关切地向大家询问那位好亲戚的情况。事情看上去并不乐观。他发现克劳利小姐的女佣(那阴着脸的女人)总是闷闷不乐,一副沮丧的样子。他还发现她的女伴布里格斯一个人在客厅里掉眼泪。听说亲爱的朋友生病,她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来了。她想赶紧跑到她的床边照顾她,以往每回克劳利小姐生病,总是布里格斯伴她左右。可这次克劳利小姐不许她进房间。一个陌生人正在管着她吃药的事——那是个乡下来的陌生人,一个可恶的小姐……克劳利小姐的女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把破碎的感情和哭红的鼻子埋在自己的手帕里。
罗登·克劳利让那位阴沉着脸的女佣上楼通报他到家的消息。随后,克劳利小姐的新女伴从病房里轻快地走来,他焦急地走上前去迎接,她则将小手放在他的手上,同时向不解的布里格斯投去鄙夷的一瞥。接着,她示意年轻的近卫团军官跟她走到后客厅里,又领着他下楼走进曾举办过无数盛宴的餐室,只是如今空无一人。
他们二人在那儿谈了十分钟,讨论的无疑是楼上老太太的病情。最后餐室清脆的铃声响了,克劳利小姐那大个子亲信鲍尔斯先生立刻跑去接应(其实他们俩聊天儿的大半时间里,他都站在钥匙孔边上)。随后上尉捻着八字胡走了出去,骑上那匹正在刨草堆的黑马,引得聚在街道上的一群流氓孩子好生羡慕。黑马优雅地腾跃而起,他将马控制住,往餐室瞅了一眼——那姑娘的身影在窗前掠过,马上就消失了,毫无疑问,她又上楼去履行她富有爱心的感人职责了。
那姑娘是谁呀?那天傍晚,餐室里准备了两个人的简餐,她和布里格斯小姐一起吃。在这位新护士暂时离房的空当儿,贴身女佣弗金太太推门走进女主人的房间,跑这跑那忙碌起来。
布里格斯情绪起伏太大,难以下咽,一口肉也没吃。那姑娘却以精妙的技巧将一只鸡切好,然后问布里格斯要蛋黄酱。她字句清晰,吓得布里格斯用勺子舀那美味酱料时碰出了一声响,又陷入歇斯底里之中,涕泗纵横。
“您是不是该给布里格斯小姐倒杯葡萄酒呢?”那姑娘对主人亲信鲍尔斯先生说。大个子鲍尔斯先生照做了。布里格斯呆板地拿起酒杯,哆哆嗦嗦地灌了下去,又呜咽一阵,然后开始摆弄盘子里的鸡肉。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搞得定,”那姑娘温柔地说,“不必劳烦鲍尔斯先生了。鲍尔斯先生,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再打铃吧,您看可以吗?”于是他下楼去了,顺便把一个无辜的下属听差狠狠地骂了一顿出气。
“很遗憾让您有这样的反应,布里格斯小姐。”那年轻女士冷淡又稍带讽刺地说。
“我最亲爱的朋友病重了,可她不愿意见我。”新一轮的悲痛袭来,布里格斯哽咽着说。
“她没什么大问题了。别伤心了,亲爱的布里格斯小姐。她只是吃得太多,如此而已。她现在已经好多了。她很快就会康复过来的。她就是拔了火罐,吃了药,精神头儿马上就会好起来的。请不要伤心,喝点酒吧。”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不想再见我了?”布里格斯小姐哭诉道,“噢,玛蒂尔达,玛蒂尔达,我尽心尽力伺候了您三十二年,您真的要这样回报您可怜的,可怜的阿拉贝拉吗?”
“别哭得太伤心了,可怜的阿拉贝拉,”那姑娘略带一丝冷笑道,“她不想见您,只是因为她说您对她照顾得没我好。我整夜不睡并不是件轻松事。我倒希望这份活儿是由您来干。”
“这么多年来,不都是我在那床边伺候着亲爱的她吗?”阿拉贝拉说,“可是现在——”
“现在她更喜欢别人了。嗯,生病的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喜好,得哄着才行。她病好之后我也该走了。”
“不要,不要!”阿拉贝拉大喊,疯狂地吸着她的嗅盐瓶[1]。
“您是说不要病好还是不要走,布里格斯小姐?”对方继续以略带挑衅的随和语气问,“唉呀真是的——她两周之内就会康复的,到时候我就要回到克劳利庄园,跟我的小学生们在一起了。那里还有她们的母亲,她比我们的朋友病得更严重。您不用嫉妒我,我亲爱的布里格斯小姐。我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可怜姑娘,我没有任何威胁。我不想取代您,让您失宠于克劳利小姐。我走后一个星期她就会忘掉我的,而她对您的喜爱是基于您多年来为她做的一切。如果您愿意的话,给我一点酒吧,我亲爱的布里格斯小姐,我们做个朋友。我保证我们能成为朋友的。”
布里格斯向来是个心肠软、容易哄的人,听见那姑娘的请求,她一言不发地把手伸了出去。但她仍然痛苦万分,为玛蒂尔达的变化无常而哀叹。半小时后,她们用餐完毕,瑞贝卡·夏泼小姐走上楼到病人的房间去(想必您吃了一惊吧,一直被我巧妙地称为“那姑娘”的人其实是她),客客气气地请可怜的弗金出去。“谢谢您,弗金太太,已经可以了。您照顾得真好!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会拉铃的。”弗金说了一句“谢谢您”便走下楼去,嫉妒如暴风雨般在心中涌动。可她只能将情绪压住,因此也变得更危险了。
她经过二楼的楼梯平台时,客厅门突然开了,难道是她心中涌动的暴风给吹开的?不,是布里格斯偷偷摸摸打开的。布里格斯一直在那儿守着呢。遭冷落的弗金下楼时的嘎吱声,以及她手里的勺子和稀粥碗丁零当啷的声音,布里格斯都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样,弗金?”她进客厅后,布里格斯便问,“简,情况如何?”
“坏透了,布里格斯小姐。”弗金一边摇头一边说。
“她不是好些了吗?”
“她只开口说过一次话,我问她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她就让我闭上我的笨嘴。噢,布里格斯小姐,我从没想过会有今天!”说完又哭起来。
“这个夏泼小姐到底是个什么人,弗金?我之前不过是去了一趟我坚定的朋友莱昂内尔·德拉米尔牧师和他亲切的夫人高雅的家里欢度圣诞,可我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当口,一个陌生人夺走了我的玛蒂尔达,夺走了我仍然最亲爱的玛蒂尔达对我的喜爱!”从布里格斯小姐的表达可以看出,她是个多愁善感、具有文艺气质的人。她还曾出版过一本诗集《夜莺》——以预订出版[2]的形式。
“布里格斯小姐,他们都被那女人冲昏了头脑,”弗金答道,“皮特爵士不肯让她走,可他又不敢跟克劳利小姐对抗。教区长家的比尤特太太一样糟,只要看不见她就难受。上尉也被她鬼迷心窍。克劳利先生嫉妒坏了。现在克劳利小姐病了,除了夏泼小姐,她不许任何人在身边伺候,我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我感觉他们个个都像是被下了咒语似的。”
当晚瑞贝卡整夜守在克劳利小姐身边。第二天晚上,老太太睡得很熟,瑞贝卡得以在女主人床尾的沙发上舒服地休息几个小时。很快克劳利小姐就恢复了神采,坐起来乐呵呵地看瑞贝卡模仿布里格斯小姐伤心的模样。看到瑞贝卡将布里格斯抽鼻子和用手帕的姿势演绎得这么生动,克劳利小姐变得情绪高涨,来见她的医生都欣喜不已。要知道这位尊贵的女士以往即便得了最微不足道的病,也会感叹世事凄凉,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克劳利上尉每天都来,听瑞贝卡小姐汇报他姑妈的病情。由于病好得快,可怜的布里格斯终于获准与她的女主人相见。读者们若是怀有一颗温柔的心,肯定想象得到这多愁善感的女子心中压抑着怎样的情感,又将如何对克劳利小姐动情地诉衷肠。
不久后,克劳利小姐又开始让布里格斯陪在她身边。瑞贝卡则总在一旁当着她的面模仿她,令人叹服的是模仿时她自己偏不笑,更让她可敬的女主人感到乐趣无穷。
克劳利小姐不幸得病,以及她离开她弟弟那乡下宅子的原因,说起来特别不浪漫,恐怕不适合在这部文雅又多情的小说里讲述。一位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怎么可能因为暴饮暴食,后来又在教区长家刚出炉的龙虾大餐上无所节制,从而引起身体微恙呢?她自己都一再说了,那只是天气太潮湿的缘故。这场病来势凶猛,用牧师的话来说,她差点儿呜呼哀哉,因此全家都投入了期盼遗嘱的热潮之中。罗登·克劳利相信自己一定能在伦敦社交季开初至少拿到四万镑。克劳利先生派人送去一包精选的宗教小册子,为她从名利场和公园路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做好准备。不过南安普敦[3]的一位好医生及时被请来,制服了那只几乎要了她命的龙虾,帮她恢复了回到伦敦的体力。准男爵并没有掩饰自己因事件转折而感到的强烈失望。
当所有人都围着克劳利小姐转,教区长家的信使每小时都将她的病情带给热爱她的亲人们时,宅子里另一个区域有位女士正病入膏肓,却无一人关心。她便是克劳利夫人。皮特爵士同意了对她的会诊,因为可以不收钱。但好医生给她瞧完病后摇了摇头。随后,她就被扔在孤独的房间里慢慢咽气,大家对她还不如对庭院里一根野草留心。
由于家庭女教师有事在身,家里的两个小女孩也失去了不可估量的宝贵指导。克劳利小姐见夏泼小姐服侍得尽心尽力,便只允许她一个人伺候自己吃药。弗金早在女主人从乡下回来之前就已失宠。不过回到伦敦后,看到布里格斯小姐遭遇了与她同样的背叛,承受着同样的嫉妒之痛,这位忠诚的女佣也获得了些许黯淡的安慰。
罗登上尉因为姑妈的病情得以延长假期,守在家里尽本分。他总是待在前房(克劳利小姐躺在大卧房,他需要穿过一间蓝色小客厅进入),他父亲经常在那儿碰见他。或者,无论他经过走廊时脚步多轻,他父亲准会把房门打开,伸出鬣狗般的脸往外瞪。这两人为什么要这样互相张望?当然是为了赢得这场回报丰盛的战斗,比赛谁对大卧房里亲爱的病人更体贴。瑞贝卡时不时走出来安慰他们,应该这么说,有时安慰做父亲的,有时安慰做儿子的。两位可敬的绅士也都心急火燎地向克劳利小姐信任的这位小信使探听病情。
瑞贝卡每天会花半小时下楼吃饭,同时维持父子之间的和气。饭后她便再不露面。罗登会骑马到马德伯里第一百五十团的营地去,留下他父亲跟荷洛克斯先生在家喝兑水朗姆酒。瑞贝卡在克劳利小姐的病房里度过了常人所能经历的最疲惫的两周,但她的小神经仿佛是铁打的,病房里枯燥而繁重的工作从未令她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