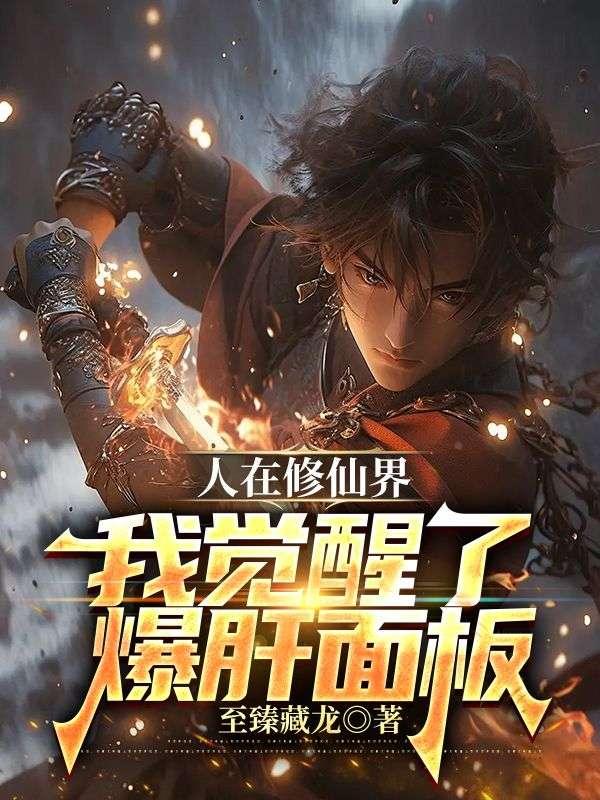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病弱渣攻he指南 > 第124章 这个杀手不太冷17(第2页)
第124章 这个杀手不太冷17(第2页)
裴渡哑然失笑:“这也是郁长烬教你的?”
沈缘看着他没说话。
裴渡心口升起阵气恼,越想越是愤恨,郁长烬那种人,生来天之骄子身份尊贵,说起来他的母亲与师娘或许还出自同一族,这样的人,非常之人非常手段,怕是早就在床榻间把小师弟吃透了。
如今还教他生气……
只怕对郁长烬来说是情趣罢了。
“行了,”裴渡无奈地把人圈进臂膀之中,轻声道:“师兄告诉你,你可别生气了。”
沈缘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像刚刚还飘在脑袋上的浮云,一阵轻风吹过来“唰”得一下就散了个干净,他只是拿这种情绪当手段来用,可看的确依旧是不理解,不然哪有人刚刚还发脾气,这会儿又像软乎乎的小猫一样主动凑过来的?
“去哪里?”沈缘的眼睛很亮,如果他脑袋上能长耳朵,恐怕早就直挺挺地竖起来了。
裴渡告诉他:“去卫家堡。”
“我要和卫翎见一面。”
……
……
卫家堡。
城墙箭楼,高耸入云,沉重钟声自远处山顶传来,凌冽寒风激荡起高墙上悬挂的“卫”字大旗,烈烈作响,守卫持弓弩立于城楼顶端,注视着来往商客。
天边云雾混沌,城外冷风横扫,大雪漫卷,直扑人面颊之上,城外有一队人纵马踏雪归城,马蹄激昂扬起碎雪,反沾了一身油亮皮毛,湿漉漉地瞬间结成了冰络子,为首之人黑衣红袖,他高高扬起手,对着城楼喊道:“——请见主上,有要事报!”
……
“问主上安,您要我监视着的那人,乘马车往卫家堡方向来了,跟着十多个守卫,暗处不知是否还有人,约摸还有半个时辰入城,是否拦下?”
卫翎坐在案前,静静地批着案本,他面前的黑木地板上是一个瘫倒在那里生死不知的下属,于一刻钟前被当场绞死,还未来得及清理,卫翎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声音温润似玉:“不必拦,让他们进来。”
小缘……
卫翎看着那纸上散开的墨迹,一直以来平静的心湖荡起了层层波纹,他抬起手做了个手势,继续命令道:“尽力给他们行方便,若有阻拦者,格杀勿论,还有……把这人扔出去埋了吧。”
卫家堡地势有些许低,这地方原是一处不大深邃的山谷,经由卫家人一代一代在这之打成了接近平原的模样,四处都是高城耸立,底下还压着数层暗楼,用以关押犯事的下属亦或是藏冷酒,其中机关数不胜数,稍有不慎便会被无数支箭扎成刺猬。
因卫翎下了命令,再加之裴渡幼时原本就生活在这里,对地形十分熟悉,是以他带着沈缘一路畅通无阻,一直从高阁处绕了几乎半里的路,从内门而进,寻到了卫家堡的主城。
“就是这里了。”裴渡把沈缘脑袋上的帷幕压低了些,几乎遮住他整张脸,才握着他的手带人走进去,卫翎正襟危坐,双袖齐齐整整地注视着门口,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守卫,整个主殿之中只剩下他一人。
风声越来越紧,像是在昭示着什么事即将要如地底岩浆般迸发,当那身衣裳自门槛间扫过时,卫翎的心跳停了一拍,桌案上的毛笔在他紊乱的内力波动下“咔嚓”一声截成了两半,点点油墨散下来,点在他的青衣之上。
“小缘……”
“哐当——!”
裴渡甩袖合上了门,将所有可能窥探的视线隔绝在外,他的步子不大平稳,是由当初跌下山崖重伤所致,脚腕间筋骨重接了两回,才造就了这般模样。
若是以往,他心气儿高又傲得要命那时候,面对卫翎总是不服气,总是搞事情给他,可这一刻,在时隔十二年,再看见卫翎的这一刻,裴渡却忍不住乐得想笑出声。
“你配这么叫吗?”
卫翎的目光始终看着帷幕之下的少年,他慢慢地站起身来,绕过桌案行走过去,停在了沈缘面前,正欲探手去摸少年脉息,旁边裴渡一巴掌把他的手打了回去,握着卫翎的腕子用力弯折,几乎已经能够听见骨头错位的响声。
“小缘,和卫家主打个招呼吧。”
沈缘乖乖地探出手摆了摆:“翎公子。”
“我也和你打个招呼,”裴渡低低地笑起来,嗓子里像是含了血沥沥的刀片,割破了他所有的理智:“师兄,好久不见。”
作者有话要说:
关系图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