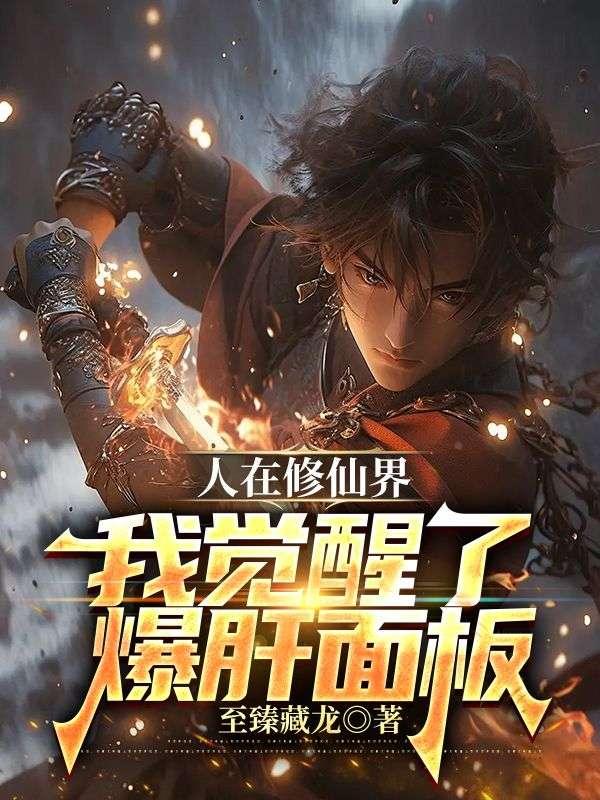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淮阴县属于哪里 > 驱马复归来(第1页)
驱马复归来(第1页)
说到元嘉公主和齐浔,那是他们这一辈高门子弟众所周知的一桩冤情孽债,只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早年间,齐夫人某日带十多岁的齐浔进宫赴宴。齐夫人在容贵嫔处续话,齐浔一人在后苑闲逛,遇到了正在闹脾气的元嘉公主。
公主当时才六七岁,脾气却不输成人,怒气冲冲地朝几名小宫女骂道:“竟敢把我的小鞠踢飞了,我让嬷嬷打你们二十大板!呜呜呜——”她此时还不太清楚二十大板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味学着母妃的口吻大吼,坐在草地上大哭大闹,“快把我的鞠找回来!呜呜呜——”一众侍女也不知是先打人好,还是先找个新的小皮鞠来。
齐浔看到不远处飘在湖心的皮鞠,又见几名内侍挤在湖边艰难打捞着,便走上前,笑容亲切地对公主说道:“公主见过皮做的蹴鞠,可见过草做的蹴鞠么?”
“你是谁?”元嘉公主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抬头乍见这位好看的小哥哥,几乎看呆了。
齐浔见她止住了哭声,走到湖边,折了几根长茅草回来,和公主一样席地而坐。茅草在他灵活的指间穿插连结,公主目不转睛地看着,不一会儿,一个玲珑秀气、带着青草香味的草鞠就编好了。
“你是仙人么?”她眨着红通通的眼睛,呆呆的,又有些崇拜地问道。
“对啊,我是专门来哄坏脾气小孩儿的仙人。”齐浔装模作样地回道,把草鞠盛在手心,递到她面前,“公主喜欢吗?”
公主没有计较他说自己坏脾气,反而笑起来,露出白白的乳齿,点头道:“喜欢!”
“那就送你了。”
她接过草鞠,当作宝贝一样,在手里颠来倒去地看着,抬头已不见齐浔踪影。
齐浔只当是哄了个小哭包,过后便忘,元嘉公主却记挂了他很久。待一年后,放在公主卧室的草裾都干黄变形了,她在山家嫁女的宴会上又遇到了齐浔。齐浔耐心地陪她玩了一会儿,转头又不见了。
此后元嘉还在宴会上见过他几次,直到十二岁那年,她向齐浔表明心意。齐浔却哭笑不得。那时他十七八岁,刚学会逛青楼喝花酒,这么个小姑娘当小妹妹逗一逗还行,若谈及男女之情,他觉得自己压根就没法把她当女人。
“浔一直把公主当作妹妹看待,从未涉及男女之情。公主千金之躯,日后定会遇到比齐浔好过千百倍的儿郎。”他拒绝得直截了当,从此得知有公主在场的宴会能躲就躲,并严词拒绝与她私下会面。
元嘉公主一贯是个执拗的主儿,用尽各种办法接近他,或是阻挠他的婚事。数年下来,元嘉公主追求齐家大公子的事迹,已传遍大街小巷。公主至今未死心,齐浔也始终毫不在意,不仅继续逛青楼,还在别院养了不少姬妾,有些欲将天涯芳草撷遍的势头。
桓清与自小出入后宫,免不了与这个表妹来往。因魏帝多年来对桓清与极为宠爱,元嘉总觉得是她分掉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父爱,故对她多般刁难,视为仇敌。桓清与虽不爱和元嘉扯上关系,但此刻刚好借她让齐浔闭嘴。
齐浔闻言,果然连忙赔笑,“都是老黄历了,清与还是放过我吧。”说着,向她举杯,“我自罚一杯如何?”
“哦,罚什么?”桓俭笑问道。
齐浔与他对视一瞬,便会过意来。“今日说到底是我的不是,此番设宴叙旧,原意是邀诸位到缦阁把酒言欢。这不,见庭檐还没来过花萼楼,萧兄也有兴趣来瞧瞧,我才约到了此处。”
听及此,桓清与眼中略带惊诧地看了萧迦叶一眼,后者依旧是坐听闲话的姿态,岿然不动。
“看什么呢,男人逛青楼多正常,你不也逛了小倌馆吗?”齐浔看见她神色立刻说道,这下轮到桓清与呆住了。
齐浔乘胜追击道:“花萼楼守卫最是缜密,一向不让女子入内。看你这打扮肯定是从隔壁小倌馆浑水摸鱼溜进来的。”齐浔一副得意的神色,桓清与暗自不爽,真让他卖弄了一回。
“怎么不说话了?桓氏儒道兼修,老师教过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肯定也教过你。所谓男女之情,性常也,并无善恶之分。”齐浔自斟了一杯酒,心中十分爽快。
“不错,情和欲本无善恶之分,但君子不宜耽情恋欲。”桓清与脱口而出,直言反驳,“进来看个新鲜自然没什么,人之贪欲正在于有一就有二,有二便有三,稍有不慎恐至迷途难返。我身为族妹,理应从旁督促劝导才是。何况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逛花萼楼若有你在旁,未免让人更不放心了。”
齐梁和许缜仅见过桓清与几面,相交尚浅,第一次听到妙龄女子在人前直言男女情欲之事,实是叹为观止,见两人几乎针锋相对,不知这番谈话将要导向何方,只睁着两只眼睛,竖起耳朵听着。
谁知齐浔却拊掌而笑,“哈哈哈哈,我还以为过了这小半年,桓县主会收敛心气。不错,这脾气还是很合我的意!”
桓清与还他一个白眼,齐浔见后笑倒桌上。
萧迦叶明白齐浔指的是桓安辞官一事,虽知他一贯爱胡闹,但这一番唇枪舌剑不论对手是否接得住,他终归都有失风度。萧迦叶没理会齐浔的笑声,转头看向桓清与一字一句道:“大魏女儿有此风范,前途自无可限量。”说罢,抬手举杯。其余几人包括齐浔,也连忙会意,举杯共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