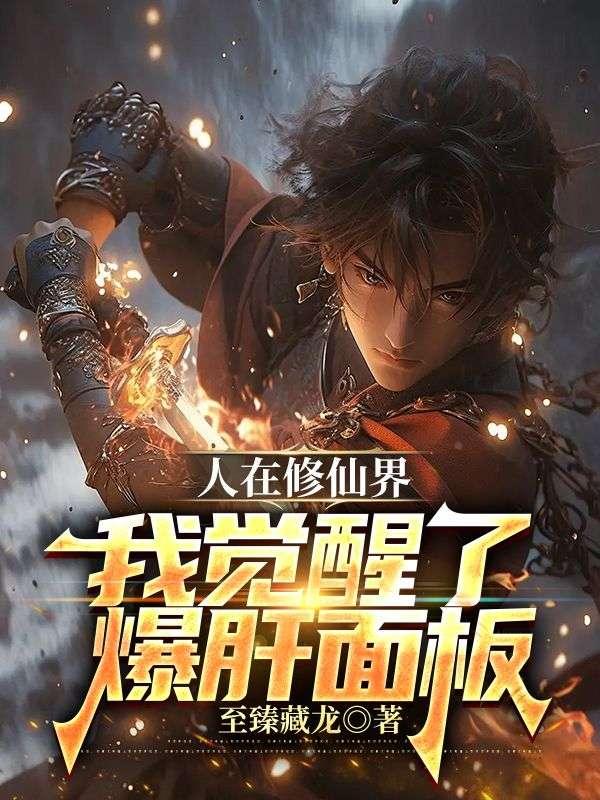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杀过的白月光来找我了裁云刀 > 第154章 松风度晚曲五(第5页)
第154章 松风度晚曲五(第5页)
“你怎么就以为我死前不会想起你?”曲不询拇指慢慢抚过她颊边,“长孙寒已死过一次了,沈师妹。”
沈如晚倏然垂下眼睫。
月光如银,映在她颊边,竟也似留下露水,从她眼睫颤了又颤,终究坠落在他掌心,小小的,一点泪珠。
那天晚上,他把她送回她的小院,没有急着走,站在院外和她漫无边际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
她也没急着进去,倚着门,目光幽然地望着他,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听着。
“再过两日,邵元康就该过来了,到时丹药、草药都足够,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他说,其实这话先前已经说过一遍了,也没有重复的必要,可他好似没觉察,“我已有了打算,又有剩下那几个杀手作人证,等七夜白开花后,事情便容易得多了。”
“嗯。”沈如晚淡淡点头。
“沈氏的事情,你不必太过担忧,”他又说,其实这话他已说过两遍,可他像是忘了自己说过,如第一遍那样郑重,“冤有头债有主,该是沈氏的罪责,主谋者自然逃不过,但沈氏弟子无数,如你一般被蒙在鼓里的也大有人在,既然是无辜的,自然也不该去承担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罪责。"
“好。”沈如晚也认真颔首。
“还有,等到七夜白的事情被揭开,你作为沈氏弟子、元让卿阁主的亲传弟子,难免要受到些非议,但蓬山同门终究还是清醒人更多,明白你取舍间的可贵,纵然有一二糊涂人,早晚也是能明白过来的,不必太过伤感。”他说。
“我明白。”沈如晚再颔首。
他终于无话可说了。
沈如晚目光幽幽地望着他。
“培育七夜白确实伤神耗力,你是该好好休息一下。”曲不询说着,慢慢抬起手,望着手腕上的那道与她相牵连的游丝,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缓声说,“先前说要一直绑着,不过是戏言,如今你要休息,我就把它去了。”
沈如晚短短地“哦”了一声,仍是不说话。
曲不询定定地看了她一眼,似是有很多话想说,可又强行忍住了,有点咬牙切齿的郁郁。说不出口。
分明是她冷不丁提起要休息,还若有似无地拿眼波瞥他,到这里,她又忽然不搭腔了。
“行吧。”他轻轻呼出口气,伸手去解那腕间游丝,没好气,“你好好休息。”
沈如晚轻轻笑了起来。
“你之前问我有没有想明白,问我确定吗?”她漫不经心地垂着眼睫不看他,“我现在确定了。”
曲不询一下盯住她。
沈如晚仍垂首,只是抬眸,从眼尾婉转地看他,眼波如春水清波,微微漾着粲然笑意。
“故意耍我?”曲不询定定问。
分明就是他以为的意思,她偏要装作无意,耍得他懊恼郁结要走,她又来勾他。
沈如晚目光幽婉。
“是啊。”她竟承认了。
“你不高兴了?”她居然还问。
曲不询没忍住一声哂笑。
他蓦然上前一步,将她圈在门边,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词吗?”他问她。
“什么?”沈如晚问。
曲不询微微用力攥住她下巴,声音低低的,一字一顿,“自投罗网、请君入瓮、作茧自缚。”
沈如晚微微蹙眉,不太满意,“我自投罗网?“
曲不询冷笑,可又不是真生气。
“哪能啊?”他说,“我自投罗网。”
沈如晚一下被他逗笑了,伏在他肩头笑得没完。
曲不询等她笑意渐止。
他垂下头,深深凝望她,直到她不笑了,清湛眼瞳里唯有他的面容,他吻她。
沈如晚心里总把他比做火焰。
烈火,最灼热、最滚烫的赤焰,万丈深渊下烧不完的岩浆,永远灼烧、永远炽烈,把一切都焚烧到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