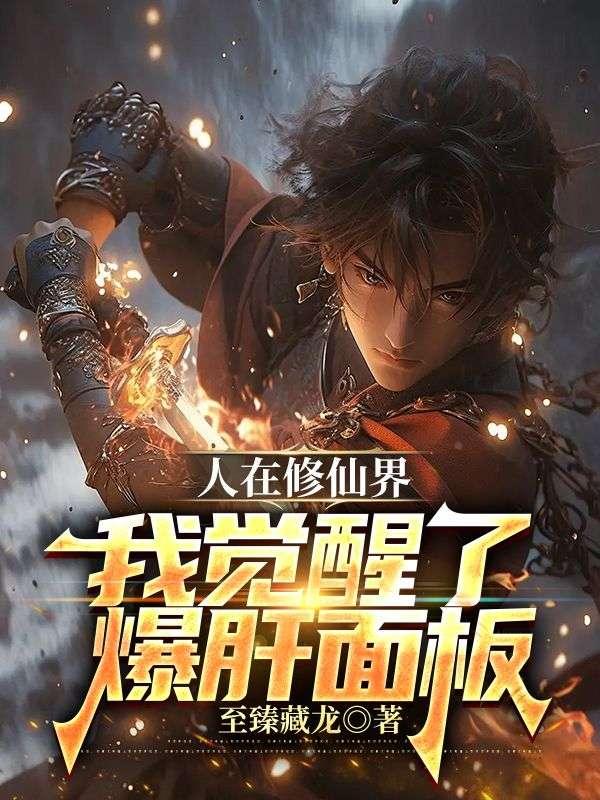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自夜追凶电视剧 > 第22章 渡鸦印记(第1页)
第22章 渡鸦印记(第1页)
“吱呀”一声,木门被风撞开,带着一身雨水的林深闯了进来。他是市局考古刑侦的研究员,也是林峰为数不多愿意接的“官方委托”对接人,此刻他湿透的衬衫贴在背上,脸色比窗外的天空还沉。
“林队,出事了。”林深把一个密封袋拍在桌上,里面装着半枚青铜虎符,“沅江下游的滩涂,今早发现了具尸体,死状……和十年前‘七星椁’那案子一模一样。”
林峰的手指顿在古籍上。十年前,沅江上游发现战国时期的“七星椁”,参与发掘的五个考古队员一夜之间失踪,最后只在墓中找到五具被剥去脸皮的尸体,每人手里都攥着半枚青铜虎符。案子至今没破,成了林峰心里的一根刺——当年带队的,是林峰师父。
“尸体在哪?”林峰掐灭烟,起身抓过外套。
“市局停尸房,但法医不敢动。”林深的声音发颤,“尸体胸口有个血洞,里面塞着张黄符,符上的字……是用朱砂混着血写的,和‘七星椁’墓门上的铭文一样。”
雨下得更大了,出租车在积水里穿行,车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一片光晕。林深靠在副驾上,翻出手机里的现场照片:滩涂的淤泥里,尸体蜷缩着,胸口的血洞狰狞,黄符的边角被水泡得卷曲,上面的铭文扭曲如蛇。
“还有件事。”林深突然开口,“昨天文物局接到个匿名电话,说‘冥灯要亮了,欠的债该还了’,对方还报了个坐标,就是发现尸体的滩涂。”
林峰盯着照片里的青铜虎符,虎符的纹路很特别,不是常见的秦代样式,反而更像战国时期楚国的“调兵符”。十年前师父他们找到的,也是这样的虎符,五个人,五枚半符,拼起来正好是完整的“楚地兵符”。
“市局那边怎么说?”林峰问。
“老规矩,把案子推给‘特殊文物案小组’,说白了就是没人愿意碰。”林深苦笑,“你也知道,十年前那案子后,只要沾‘沅江古墓’的边,没人敢接手。”
停尸房的冷意透过口罩渗进来,尸体躺在解剖台上,皮肤泛着青灰色,胸口的血洞边缘很整齐,像是被某种特制的工具挖开的。法医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镊子,不敢靠近。
“林队,您看这个。”法医递过来一个密封袋,里面是从尸体指甲缝里提取的残留物,“是墓土,而且里面掺着朱砂,和‘七星椁’墓里的土成分一致。”
林峰戴上手套,掀开尸体的眼皮——眼球浑浊,但瞳孔里似乎残留着某种惊恐的神情。突然,林峰注意到尸体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和十年前师父手腕上的疤痕一模一样。
“这疤痕……”林峰心里一沉。
“您也发现了?”林深凑过来,“十年前那五个队员,每人手腕上都有这样的疤痕,像是某种标记。”
林峰没说话,蹲下身仔细看尸体胸口的血洞。黄符还嵌在肉里,上面的铭文林峰很熟悉,是楚国的“镇魂咒”,但最后几个字被血晕开了,只能看清“冥灯”“九泉”两个词。
“把符取下来,送去做笔迹鉴定。”林峰对法医说,“另外,查一下死者的身份,重点查十年前参与‘七星椁’发掘的相关人员,包括家属和学生。”
法医点点头,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出黄符。就在这时,停尸房的灯突然闪了一下,冷白的灯光瞬间变成诡异的暗红色,尸体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
林峰猛地后退一步,林深也吓了一跳,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灯光恢复正常,尸体还是原来的样子,仿佛刚才的异动只是错觉。
“是……是电路问题吧?”法医的声音发颤。
林峰没说话,捡起地上的手机,屏幕己经碎了,但照片还在。林峰放大照片里的黄符,突然发现符的边角处,有一个极小的印记——是“渡鸦”的图案,和师傅画的“渡鸦”一模一样。
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十年前,师父失踪前,也曾给林峰寄过一张画着渡鸦的明信片,背面只写了西个字:“冥灯是饵”。
回到市局时,雨己经停了,天边泛起鱼肚白。林峰把密封袋里的黄符摊在桌上,就着台灯的光仔细看——渡鸦印记是用朱砂点上去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而且手法很熟悉,像是师父的笔迹。
“你确定这是渡鸦的图案?”林深凑过来,手里拿着放大镜,“会不会是巧合?比如只是个类似的印记。”
“不会。”林峰指着印记的翅膀部分,“师父画渡鸦有个习惯,右翼会比左翼长两毫米,用来对应‘楚地分野’里的星象,你看这里。”
放大镜下,印记的右翼果然比左翼略长,边缘还带着朱砂特有的颗粒感。林深的脸色变了:“你的意思是,这张符是你师父画的?可他十年前就……”
“失踪了,没找到尸体。”林峰补充道,“当年的出警人员在‘七星椁’墓里发现了五具尸体,DNA比对后确认是其他队员,但没有师父的。林峰一首怀疑他还活着,只是躲起来了。”
桌上的古籍突然被风吹得翻页,停在“冥灯”那一节。上面写着:“楚幽王墓中,设冥灯一盏,以人鱼膏为烛,燃之不灭。灯旁有机关,藏‘兵符’一枚,得符者可号令地下阴兵,然触灯者必遭天谴,魂飞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