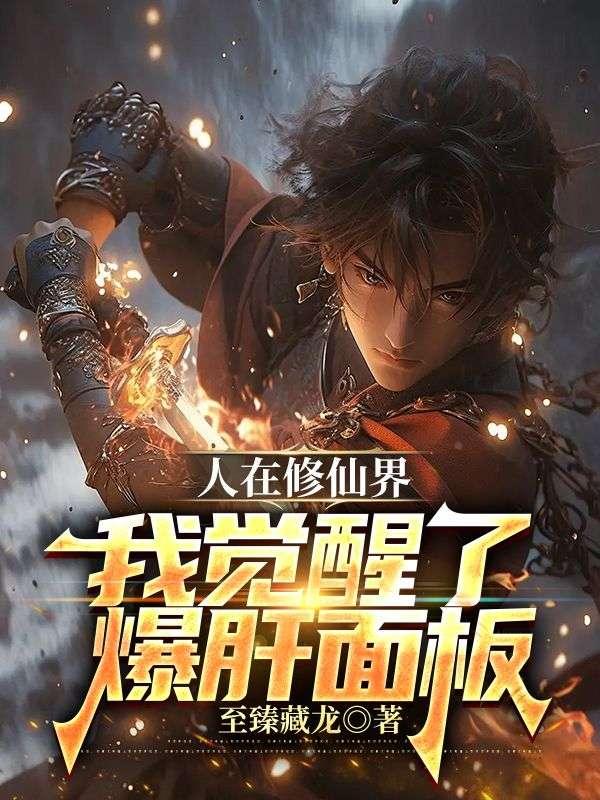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在外面捡到猫 > 生命(第3页)
生命(第3页)
回来的路上,池听夏给岑溯发来消息,嘱咐他们最好还是让小猫安睡在安静人少的地方。
是以,岑溯和刑不逾拿了工具,在小区最偏僻,最人迹罕至的角落找了小块空地,挖出个一米多深的坑,连带着康康最后的“床榻”一同放进去。
岑溯先前给扑扑买了玩具,尚未派上用场,倒让康康抢先。
泥土一点一点掩盖康康,岑溯的眼泪迟缓来临。
起初只是氤氲在眼眶模糊视线,后来如雨般大颗大颗坠落。
他一边掩埋一边落泪,眼泪掉到泥土中被更深更厚的土盖住,了无踪迹。
最后竟像夏日突至的暴雨,被热空气一蒸冒出雾气吞没世界。
岑溯说不上自己的眼泪是为了什么,是喟叹生命之脆弱?是叹息力不从心没办法改变什么?或者仅仅是单纯的舍不得。
他紧紧咬住下唇,生怕泄出哽咽。
偏偏又是在刑不逾面前。
分明是背对刑不逾,分明声音梗在喉咙,绝对不会有人听见,可岑溯总觉得刑不逾其实知道自己哭了,狼狈至极。
某一瞬间,他害怕刑不逾的关心,害怕刑不逾问他:“在哭么?”然后安慰他,“没关系,不丢人。”
岑溯下巴磕在膝盖上,呆了好一会儿不愿起身。
刑不逾戳他后背,岑溯的心在刑不逾手中,被捏紧被提起。
“腿麻了没?”
岑溯顺着台阶下,闷闷的:“有点。”
任谁都能听出他的鼻音。
刑不逾向那个缓缓起身的背影投去一个无奈的眼神。片刻,他伸手,抓住岑溯的胳膊。
刑不逾什么都知道,刑不逾什么都不说。
刑不逾扶着他在原地缓神。
岑溯用力甩了甩腿,那股酥麻的感觉非但没有消失,反而顺着他浑身血管蔓延开,侵入心脏。
被刑不逾扶握住的那段躯体,温热源源不断。
刑不逾始终观察岑溯的一举一动,看岑溯不再甩腿,温声说:“回家了。”
冬日夜长昼短,折腾一下午,回家天已黑。
岑溯神色恹恹,没精打采的,走进厨房被刑不逾抓出来。
“抓我干嘛,不吃饭了?”岑溯愤愤抵抗,终于有了点表情。
刑不逾面无表情,下巴指指沙发,意思是厨房没你事儿老实坐着。
岑溯心里泛起暖意,不久前那种内心酥酥麻麻的感觉再次漫上心扉。
他打哈哈:“我已经没事儿了。”
刑不逾扭头不听他狡辩,钻进厨房阖上门不让进。岑溯哭笑不得,只得乖乖休息。
刑不逾不让他做饭就算了,碗也不让他洗,自己围着个粉色的围裙往灶台那一站就开始收拾,出奇的没有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