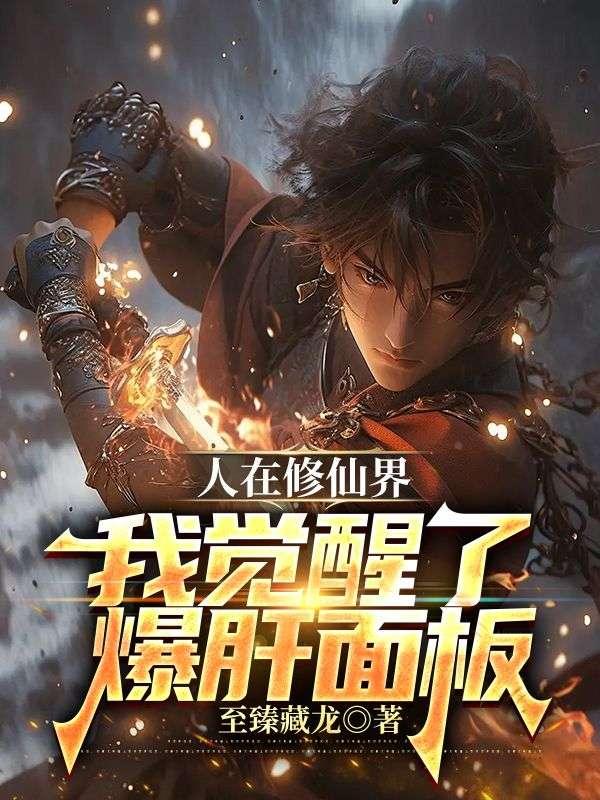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带着妹妹匡扶大明笔趣阁 > 150160(第11页)
150160(第11页)
“这话问得——”赵明州的声音里含着隐隐的笑意,“你不是还跑到肇庆城救我们吗?”
“可是……可是我今天晚上又跑到爹……孔有德这里了,这般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简直……简直就是吴三桂那般的三姓家奴!”孔四贞愧疚得咬牙切齿,周围人却是愣住了,半晌没人接话。
“你们尽可以骂我,我知道自己做得这事儿……猪狗不如!”
齐白岳笑了,眉眼促狭地挑起,冲赵明州使了个眼色:“我本来想替阿姊骂几句,可惜啊,词儿都被她自己骂完了。”
李攀也憨厚地笑了起来:“可不是,分析得这么透彻,末将倒是觉得孔小姐知错了。”
赵明州没有应声,只是放松了手臂,任马前行。可孔四贞即便不回头,也能猜到她脸上的表情,这反而让她的心里愈发难受。孔有德是自己的亲爹,面对背叛尚且能痛下杀手,可明州军对自己的反复无常,只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容,甚至舍命相救。
“我背叛了你们啊!”孔四贞倏地回头,瞪向身后的赵明州。
可怜赵明州平日里身手了得,这一次竟是被孔四贞的发辫抽了个正着。赵明州又好气又好笑地“嘶”了一声,正对上孔四贞红得如兔子般地双眸。
“背叛谁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要背叛自己的心。”赵明州咧了咧嘴,她的脸颊上有一块被烟火熏黑的痕迹,随着她嘴角的一张一合滑稽地颤动着。孔四贞却丁点儿笑不出来,只觉鼻腔酸得难受。“不论你做了什么,孔小姐,我们都知道你心是好的。”
孔四贞心头懊恼得紧,强迫自己将脑袋转向一旁的赣江,死死睁大眼睛防止不争气的眼泪再次滑落。模糊的视野里,突然涌入了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她的呼吸骤然凝滞了。
江水的流速似乎缓了下来,连拍打江岸的浪花都偃旗息鼓,显得有气无力。在江水回环拐弯之处,有某种莹白色的巨物在蠕动,似是潜伏在水中的怪鱼,又如同肆意生长的巨大蘑菇。孔四贞眯着眼睛,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下一瞬,被那巨物阻塞良久的江水终于积蓄了足够的力气,“噗”地一声冲开了缺口,倾斜而下。而那“巨物”也随之四分五裂,东一片西一堆摊开去,像是随意洒落在锅底的面糊。
借着漫天璀璨的星斗,孔四贞看清了。那些鼓鼓囊囊,肿胀发白的可不是面糊,而是成百上千具肿胀溃烂的尸首。
江水裹挟着腐肉与断肢,在尸堆间挤出黏腻的咕噜声。最上层的尸体尚未完全发胀,苍白的脸孔仰面朝天,空洞的眼窝里蓄着水荇,仿佛永远流不尽的绿色的泪滴。扑面而来的腥臭味儿像一把生锈的刀,剐进孔四贞的鼻腔,让她疼得失声尖叫。
不知何时,胯下的花斑马停住不动了,赵明州翻身下马,擎着火把向江边走去。火把的光圈扫过江面,更多的细节在火光中狰狞毕现:孩童蜷缩成团的焦黑尸体,老者被削去半边的头颅,妇人怀里紧搂的婴孩只剩森森白骨这些尸首都缺了一边的耳朵,这正是清军对待“叛民”的标志。
远处的河流正卷来更多的尸体,有许多尸体甚至还穿着清军的衣服。
赵明州的指甲深深嵌入
掌心之中,那多年前的噩梦又回来了,那屠戮了整个扬州城的恶魔又回来了!
她还欲俯身再看,胳膊却被一人紧紧抓住。
“阿姊,不可,你看他们的脸!”
齐白岳死死拽住赵明州,不允许她再往前踏出一步。
那些与他们望着同一片星空的尸首,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痘疹,痘疹大多已经溃烂外翻,像极了婴孩儿嚎哭的嘴巴。
目睹了这一切的孔四贞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赵明州面色铁青,翻上马背,大声道:“立刻回营!”
***
沿着奔腾汹涌的赣江缓缓向上,绕过数道急促的转弯,攀过两座陡峭的山梁,一片人数众多的清军营地便显现在眼前。
多铎沉默地凝望着不远处忙碌的士兵,手中浸透了药汁的锦帕紧紧覆住口鼻。
那群如临大敌的清兵,个个手持长枪,眼神中带着麻木与恐惧。在他们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有穿着破旧衣衫的难民,也有身着清军服饰的士兵。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堆叠在一起,如同当年扬州城外熊熊燃烧的京观。
负责处理尸体的清兵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用长枪的枪头挑着尸体的衣物,费力地将尸体往河边拖去。有些尸体因为停放时间过长,拖动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僵硬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面对这样的场景,即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亦难以掩饰面上的恐惧之色,尽可能地拉远自己和尸体的距离。
而远远望着的多铎,眸色中除了不耐,便再无其他情绪。
“嗡嘛尼叭咪哞,贫僧参见贝勒爷。”身后传来一声佛号,一名身着黄色袈裟,头戴僧帽的大喇嘛双手合十,向着多铎躬身行礼。魔·蝎·小·说·MOXIEXS。。o。X。i。e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