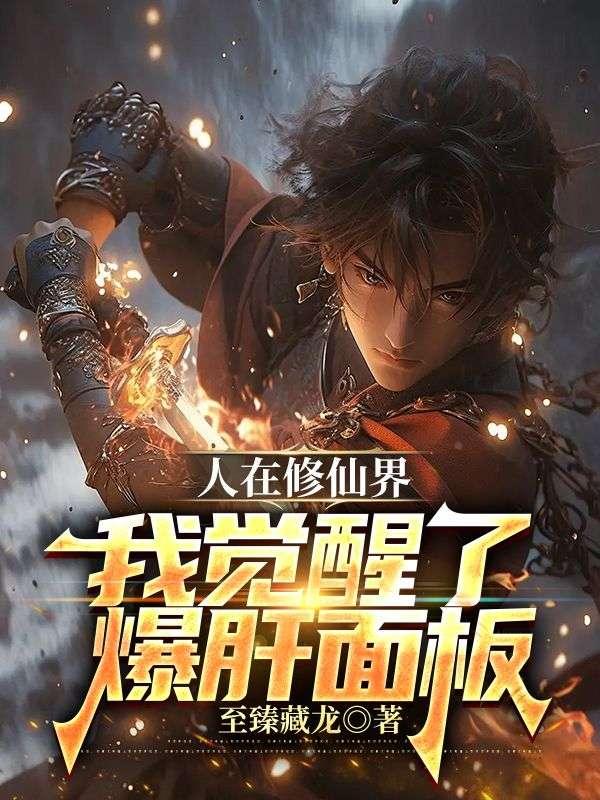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高门寒婿的科举路免费阅读 > 180190(第11页)
180190(第11页)
“兴商,未必全无好处……”
刑部尚书刘渠说道:“陛下,臣以为可一步步兴商,至于在边境上开市,容许与更南的安南国通商之事,宜暂缓。”
他们担忧的是大理段氏尚未料理干净,再来个安南国,岂不更混乱难以治理。
又有几名大臣附和他,同意在滇地兴商,但反对开边市。
“那就这么答复老师,”皇帝萧敏说道:“你们户部也给杜爱卿和沈爱卿说一声,让他二人该怎么操办怎么操办。”
众臣齐声道了声“是”后,各自退下。
……
这日,皇帝萧敏来到临华殿,看见笸箩里头放着一幅鲜亮大气的绣活儿,问:“阿琼,你怎么亲自做起针线来了?”
“妾听说绣娘们近来在为母后绣衣裳,”郑琼说道:“也想为母后做点儿什么,想来想去的,妾不大会缝衣裳,只好绣一幅像,他日福满大了,妾可以告诉他,这是陛下的娘亲,他的亲祖母……”
“也好让太后的孙辈们寄托哀思……”
皇帝萧敏听了后大为动容,他拉着郑琼的手,握在手心里哑声道:“好。”
郑琼把头靠在他膝上,温柔地说道:“陛下,咱们的皇儿快三岁了,妾想着若有福气再为陛下生个孩子,陛下子嗣繁茂,母后在天上也会高兴的。”
这话真的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这些年来,他很是思念母亲,遂伸手抚着郑琼的青丝,说道:“阿琼,你这份心很难得,朕必不辜负你。”
之后待她更加上心。
郑琼也很知趣,还请太医院给她配了些暖宫助孕的药,以求早日怀上孩儿。
皇帝萧敏得知后跟丁吉说道:“后宫之中郑昭仪待朕最是真心。”
未几,他遣往儋州为郑琼寻亲的官吏回来了,说郑家原本是当地的一个小户人家,她父亲是个秀才,娶亲后不到半年就过世了,她母亲一个人生下她之后也撒手人寰,尚在襁褓之中的她唯一的亲人,她的叔父过活,四岁那年,她叔父竟一病不起,临死之前实在揭不开锅就把她卖了……也就是说,郑家的的确确是没人在世了。
皇帝让丁吉去翻本朝郑姓的显赫世家,还真给他找到了:开国黎阳公郑恩郑家,当年有一个儿子郑阳曾外出游历到过儋州,皇帝萧敏一拍御案,就靠这句记载编出一个故事来,说当地民风开放,郑阳与当地一女子一夜风流后留下子嗣,这孩子后来长大了在那里繁衍生息,就是郑琼的祖上……郑琼摇身一变,成了黎阳公郑恩的后人,这出身够看了。
只等寻个时机,便可封她为妃,连位妃都想好了,就封她为德妃。
封妃之前,他先命人放出口风试探群臣和后宫。
周淑妃听说后一连数日睡不着觉,眼睛四周忽然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片细纹,似乎一下子褪去了十几岁明艳娇俏的少女之姿,有了妇人的疲态。她清晨梳妆时揽镜一照,被镜中明显枯萎的容颜吓了一跳,惊呼:“阿枚,我怎么……怎么老成这样了?”
其实入宫十四载,她本已是三十岁的半老徐娘。只是从前她保养的好,瞧不出年纪罢了。
周枚惶恐地跪下来:“娘娘青春年少着呢,只是有些脸色不好,必是太医院没有用心为娘娘调制上好的玉容粉,奴婢这就去传他们来治罪……”
“罢了,”周淑默然片刻后妃灰心地说道:“给我上妆吧。”
第186章
在这场暗流涌动,时急时缓的漫长而惊险的争储中,彼时失意的不只有周淑妃,还有庄王萧承钧。
他原本想借周淑妃的手除掉郑琼母子,但宫中迟迟未有音信递出,还叫他等来了郑琼即将封妃的消息,他有些焦躁,使了银子去打听,才辗转得知周淑妃非常奸猾,她不接这个手,看样子还把这件事捅给了郑昭仪,让郑琼对他怀恨在心。
他神色凝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丝丝恐惧。他想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万一等到郑琼母子羽翼丰满,到时候反过来对付他的时候,他或许没有招架之力。
庄王问谋士陈世仪:“派去鹤州的岑举人那边,怎么说?”
“昨日回信了,只是殿下有所不知,”陈世仪回道:“沈大人不会作诗,至今没有人听过他做的诗,岑举人对此也束手无策啊……”
沈持从未有诗作传出,更不要说“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①”之类的爱慕女子的诗句出自他手了,用这一招在他身上未免太假了。
庄王听了气得心口疼:“……”谁会想到一个状元郎竟不会作诗。
其实,岑稚以“沈持不会作诗,几乎从未作过诗。”这个理由回绝,既是实情,也有他看不上庄王做事的原因所在,在他的想象中,庄王应该是用非常高明圆滑的手段,把沈持神不知鬼不觉地困在西南,不让其回朝,或者从高位上拉下来,谁知并没有,而是选了这样龌龊而愚蠢的办法,连他都不禁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叹气,心中怫郁,此时才懊恼自己过于急功近利,投错了人。
然而上贼船易,下贼船却难。岑稚由是精神萎靡,心中时常惶惶不安。
……
“这个岑举人,”萧承钧说道:“对本王没什么用处了。”
陈世仪说道:“是,殿下,他日寻个错处打发他就是了。”没什么要紧的。
过了片刻,萧承钧眼珠子一转,起身背着手踱了两步说道:“人不狠,站不稳。宫中的御医,有咱们熟识的吗?”
宫里的探子说郑琼最近在吃滋补暖宫的药,想是要怀龙种了,好,很好,汉宫霍显趁皇后许平君产子时下毒除掉她的手段,正好拿来一用,定能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