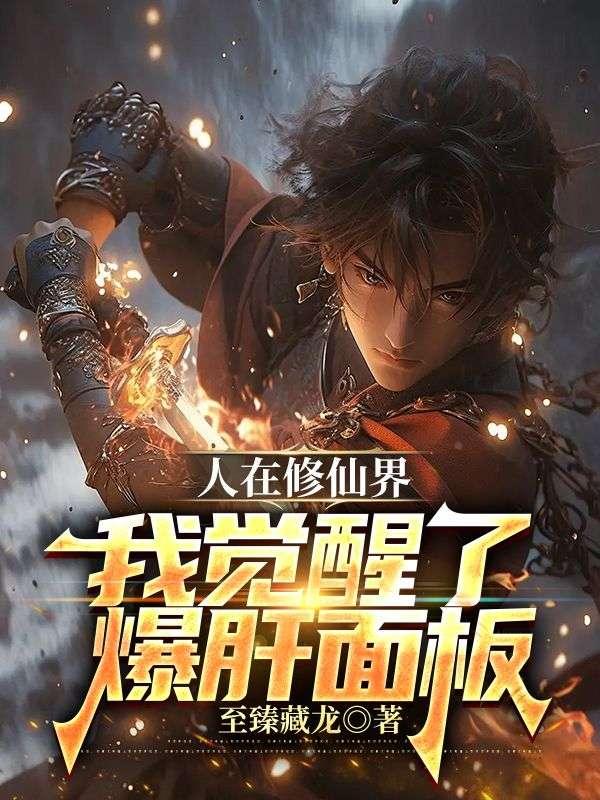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世家子弟考科举免费 > 6070(第12页)
6070(第12页)
“嗯。”宁毓承回了声,撑着椅子扶手坐直了身。
福水赶紧点了烛台,黄蜡散发着阵阵幽香,将书房照得透亮。
宁毓承道:“等下赵三爷要来,你去与阿娘说一声,我就在松华院用饭。你顺道去灶房,让饭菜赶紧送上来。”
福水应是退下,没多时,福山领着赵丰年来了。宁毓承招呼前去正厅,道:“三爷,我们边吃饭边说。”
赵丰年猜肯定是出了事,他也不推辞。福山提着饭菜进屋摆好,两人一道上桌用饭。
宁毓承用酸笋鸭汤拌饭吃了一碗,便放下了筷子,见赵丰年也大致吃得差不多,便道:“方通判死了,被黄驼背杀了。”
赵丰年缓缓抬起头看过来,神色除去震惊,还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七郎,我真没让黄驼背动手。以前我想过,被岳丈骂了一通,我便打消了念头。”赵丰年忙屏住笑解释道。
“不过,黄驼背他如何敢?”赵丰年疑惑不已,哪还吃得下饭,拿着筷子比划。
“官来如梳,兵来如篦。官员到了地方,好比梳子,在地方扎扎实实梳理一遍,土都得刮走一层。穷人日子不好过,有一口吃的,有一口气在,他们都老实本分得很,见到官,畏惧得大气都不敢出。说句大不敬的话,休说方通判,就是一条狗,给穿上那身官服,他们也会服服帖帖,俯首听命。”
宁毓承其实也感到意外,照着他们的意思,放出义庄尸首不见之事,方通判肯定会感到不安,查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方通判既然知道了有人知晓他的所作所为,借机在威慑他,就算查出黄驼背范老臭,投鼠忌器,他也不敢再随便杀人。
谁曾想,黄驼背居然敢动手杀方通判!
“呵呵,只怕贺知府的日子难过喽!”赵丰年幸灾乐祸道。
“再难过,他也是知府。”宁毓承道。
赵丰年讪讪道也是,“七郎可知贺知府打算如何处置此事,我以为,他肯定想要只手遮天,将这件事瞒得密不透风。毕竟事情传出去,他也跟着没脸,朝廷那边还会找他的麻烦。”
“先别管她。”宁毓承说了句,脑中回想着贺道年告诉他之事,问道:“那个范老臭,三爷可只他在何处?”
“底下的人打过交道,我这就让人去找。”赵丰年说完,迟疑了下,问道:“七郎可是以为范老臭知晓缘由?”
“我要问过才知。”宁毓承大致知晓了些黄驼背的杀人动机,他想要再确认一下,又道:“别惊动了他,我们一起去。”
赵丰年忙叫来贴身小厮吩咐了几句,与宁毓承一道前去了范老臭住的巷子。
范老臭收夜香,被邻里嫌弃太臭,住在城西一条破旧小巷最里面的小院。小巷中只有几间破宅子,住着如他一样,拾荒收夜香等穷人。
天黑之后,小巷除去寒风,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范老臭解开用绳索捆着的破院门,惊慌不定望着院外的几道人影,颤声问道:“贵人找谁?”
“找你,你别怕,我们就问几句话。”宁毓承说道,他转身要了盏灯笼,对赵丰年道:“三爷,其他人留在外面,我
们进去说。”
赵丰年让小厮守在外面,范老臭见破门也挡不住他们,便侧身让他们进来。
宁毓承提着点亮的灯笼,随着范老臭,从院中摆着装夜香的大木桶与恭桶中挤过,进了屋。
屋子矮小,东西厢房已经垮塌,只得一间能遮风挡雨的正屋。屋中杂乱,用石头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堆着破烂硬邦邦的被褥。范老臭勉强扫出两张凳子,拘束不安地请宁毓承与赵丰年坐,他则瑟缩着坐在了床上。
赵丰年站在那里没动,见宁毓承在凳子上坐下,才捏着鼻子坐了。
宁毓承开门见山道:“你与黄驼背交好?”
范老臭虽笨,但黄驼背聪明,曾经提醒过他,千万莫要乱说话。
赚钱心虚,范老臭小心翼翼问道:“贵人高姓大名?”
“黄驼背犯了事。”宁毓承缓缓说道。
范老臭顿时脸色大变,紧张得连话都说话都打颤,“黄哥,黄哥他犯了何事?”
院中飘散着屎尿味,赵丰年连气都不敢喘,他只巴不得赶紧离开。见范老臭还妄图耍小心机,顿时沉声道:“他犯的事,你应当清楚。你们一起做的事,难道你想撇开?”
范老臭肩膀一下塌下去,双腿发软,欲将下跪求情,被宁毓承抬手拦着了。
“你只管如实告诉,黄驼背平时除了当差,还做些甚,喜好,可有其他亲密来往之人。”宁毓承温声道。
范老臭哪敢再隐瞒,一股脑将黄驼背平时的喜好说了:“黄哥无父无母,除与我熟悉,再无与其他人来往。黄哥只喜欢钱财,连路边有根草,他都要捡起来,再脏都朝家里搂,大家都嫌弃他脏臭,晦气,我与黄哥一样脏臭。晦气,能说几句话。”
因着紧张害怕,范老臭的话说得颠三倒四,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
宁毓承却恍然大悟。
范老臭道:“黄哥将钱都换成了金子,他动不了时,就吞金自杀。黄哥说要带金子下地府,给阎王送礼,再次投胎为人,阎王以后给他勾一户权贵之家,尝尝做人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