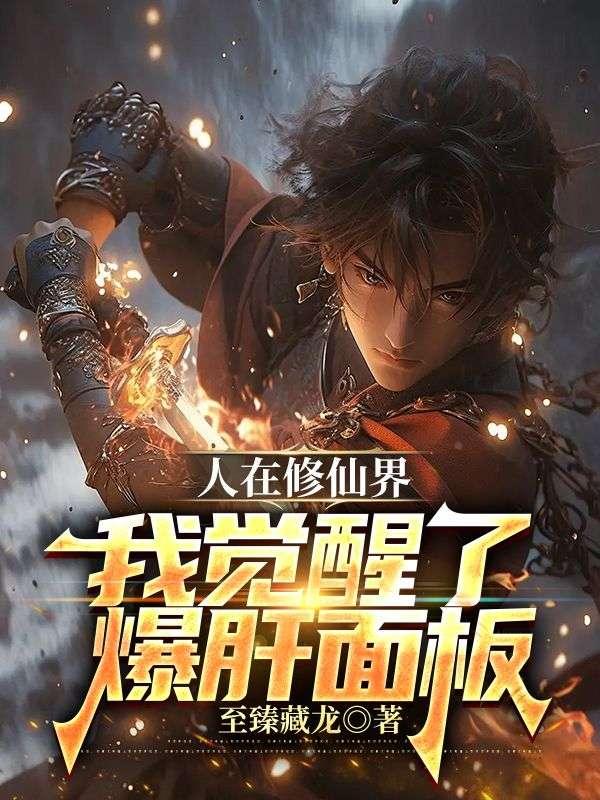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让我看看你 > 第32章(第2页)
第32章(第2页)
衣服这种挨着身体的私人物品,好像带着一种特别的亲昵感,平时没注意到的细节都会放大。
这外套在他怀里,扑面而来的是茶室里闻到过的那股白茶味,继而更清晰的是一阵淡淡的药苦味。
和谢以一起挤在房间里那张双人桌的时候,离得近了,他就会闻到一样的白茶味。明明很淡,但太清冽纯粹了,反而忽视不掉。
但他没闻到过这药味,像无意中闯进了某种陌生领域,又好像俄罗斯套娃,拆了一层,又近一步。
官周第一反应就是让这衣服哪来的回哪去,他连官衡的衣服都不会穿,哪里会穿他的,作势就要把外套提起来扔回去。
谢以早有预料似的,摁住了他的手,劝哄道:“山风冷,穿一会儿,到了院子就脱。”
官周觑着他,他又笑了笑,说:“你就当我请了个临时衣架子行么,这么漂亮双眼睛,怎么总威胁人呢。”
谢以自觉接了外套,拎着肩线覆在了官周肩上,一板一眼践行了请个衣架子。不等小少爷反应过来,扶着他的肩颈,往前推:“走吧,再赖天就亮了。”
官周挣扎了几秒,却在被推着走了几步后,又无声地静默下来。
第一次来的时候踩过的那条青石路,现在是他和谢以一前一后地走着。
没有人再开口,安安静静的,只听得见风过松林掠起的沙沙声,与沿途踩碾而过的枝叶破碎声。
路过的树梢上挂着驱虫灯,几步又一盏,作为这条路上的唯一光源,向同一个方向延展。萤火似的微弱澄光萦绕在白色毛衣的边缘,映亮了毛衣的羊毛绒边,衬得整个人都柔和了。
官周听着跟在背后的脚步声,很缓,又轻,不紧不慢的,又偏偏忽略不掉。
谢以这个晚上有些怪。
太沉默了。
先前在车上说了一番话,他没回,他竟然就也不说了。平时恶劣得只要待在一起,就少不了要逗得他翻脸,这会儿都快走到头了,也没有开口。
他突然想到,这人是不是在生气。
官周抿了抿唇,生硬地偏过头,看向那扇红木门的方向。
越来越近,从一个渺小的点,逐渐清晰。
谢以垂着眼,注视着眼前晃动的白鞋后跟,突然听到眼前人的身体里,硬邦邦地传来一句话。
“不会了。”
特别硬。
他不合时宜地想到了陈姨压咸菜的那块石头。
不仅硬,还咸。
谢以没反应过来:“什么不会了?”
官周面无表情,每一个字都吐得很艰难:“不会直接走。”
谢以反应过来了,这是在回应他那句“出来怎么不跟我说”,失笑道:“好。”
就一个“好”?
官周又闭上了嘴,毛衣外套的袖口顺着动势总撞在他垂在身侧的手上。他挪了几下,躲不开,最后破罐子破摔直接拽住了袖口。
羊绒的毛衣很软和,不扎人,嵌在手里闹得人掌心很痒。他的手指没进柔软的布料里,攥得很紧,以至于关节处微微泛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