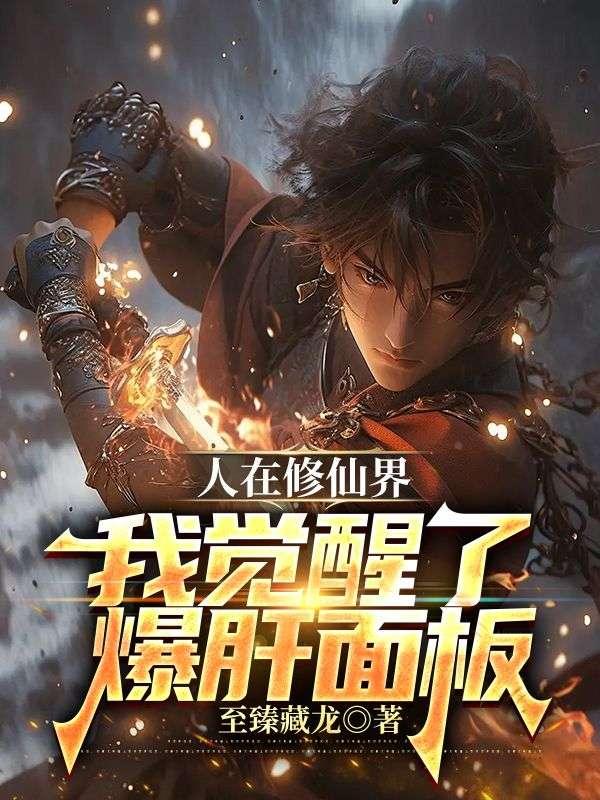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上何忌骨肉亲书电子版免费阅读 > 第56章(第2页)
第56章(第2页)
母亲冷笑道,“哼……对不起,你想了很久吧……”。
“这一切能抹掉吗……可能吗……”,母亲的声调开始提高了一点,上身的起伏也明显了。
“这就不是正常的母子能发生的事……既然不是正常的母子了,那就不是母子……”,母亲脸上的肌肤几乎都要颤抖起来。
不知为何,此刻我想大胆地辩驳,今晚,今晚是个巨大的意外,是你的“误解”,是你的“不抗拒”,才会令事情无可挽回。
但这话始终无法干脆利落地挤出,“今……今晚是因为……”。
不知母亲揣测我要说的什么,她染着干涸泪痕的脸突然迸发出神经质的冷笑,脖颈青筋随着沙哑的声线剧烈跳动:“黎御卿……只是今晚吗,你淫邪的思想,行为,都多久了大家心知肚明”,手指痉挛般揪住胸口衣料,破碎的音节混着唾沫星子飞溅,“你就是死性不改,你没救了,你今天敢对你妈做出这种事,日后不知还要犯下什么天大的罪!”。
是啊,我能有什么理由呢,这种事什么理由都站不住脚,承认错误吗,承诺痛改前非吗,或许是个正确的能取得谅解的法子,可是我内心好像有某种坚定,不舍得说出这一出。
很荒谬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母亲能说这么多,能直面这件事。
当压抑被冲破,人的脑子就开始灵活了。
食髓当然知味,内心的信念是,我不甘就这么看着最美好年华的母亲,如场地在我最血气方刚的年纪飘过。
怀璧其罪,如果我没见识过她蓬勃的女性魅力一面,如果她没有丰腴媚熟的娇人,我尚且能将这种情结当作偶尔的幻想。
可偏偏,她对上了少年的性癖。
我用苦涩乞求的眼神及语气,对母亲说道,“啊妈你都知道…我一直以来这些青春期的冲动…”。
“可哪有怎样呢……我不是成绩更好了吗,我不是人都更加积极阳光了吗,我不是里里外外都更加像个懂事的儿子了吗……”。
“也……也就除了那点事……”。
当一件事没有绝对的理论来定义,那么所有说辞都能被解构。
母子的过于亲密,只有一个男女授受不亲,只有一句身份和血缘铸就的人伦禁忌不允许过于亲密。
可母子的不伦关系,终究没有人敢于搬上台面来剖析,然后定义它的禁区属性。
恋母情节倒是挺多论述,可这不恰好证明了其存在的可能性吗;当事件收拢于家庭的私密空间,那它还能像洪水猛兽吗。
其实简单来说,放在小家庭小空间里,假设不为人知,你无法批判这个事,或者批判的理由都很苍白。
在我的认知中,我敢于最终踏出这一步,其理论根源正是如此。
而对于母亲这样的乡镇妇女来说,恐怕也很难说清她儿子如果对其他女人犯下淫邪行为,与对她犯下,这两者之间在罪恶上有多大区别。
噢,区别是,对其他女人犯下这种事,很大概率直接被法律惩处……这也是她从一而终“有限度”地容忍我所作所为的认知基础。
当然,老生常谈的是出于母爱……但我始终觉得没那么简单。我不试图完全解构这种行为,我向来是见步行步,见招拆招,达成不伦的目的。
母亲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平静出声,“你想过后果吗……万一你爸今晚回来就发现……万一别人知道……这个家就彻底没了!”。
“黎御卿……你口口声声说懂事……可是你就是这么的自私……令人发指!”,母亲又睁开眼,目视前方,苦笑着摇了摇头,儿子这幅行径令她无法接受,不敢相信自己真有一个这样的儿子。
我将脑袋埋得更低,耳边响起嗡嗡的耳鸣声,淹没了母亲的质问。那丝机智又被冲散了,少年怎么可能游刃有余地面对这一切呢。
我觉得我又开始说胡话了,“是……我不应该不分状况不分时段地放纵自己的冲动……”。
但我说话留余地的天赋没有丢失,这像是在说,我以后会找恰当时机的了。
母亲愣了一下,好像多少能读懂我一些言外之意,但不敢确定又没挑破,只得手扶额头,有些无力丧气地说道,“我不会教育你了……发生了这种事……你说我们以后怎么相处……”。
我回道,颇为理直气壮,“什么怎么相处。我不还是好好的乖乖的吗,那怕是有青春期冲动以来”。
话说开了,机智总会回来一点,我再度提及青春期冲动。
寄望于作为过来人的母亲,应该多少能理解这一点。
母亲冷眼扫过,“乖儿子?能对他妈做这种事?”。
“不是吗,你不是看在眼里吗,妨碍我学习更好了吗,妨碍我也开始操心你的工作想给你分担更多了吗”,我梗着脖子说道。
“你就没安好心!一直憋着坏!”她突然笑了,眼尾皱纹挤成锋利的折线,“今天我算是彻底确认了我有这么一个儿子。造孽啊”。
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幼犬般的呜咽,那是8岁摔坏她手镯时的声调:“无论发生什么…你永远是我妈……这一点怎样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