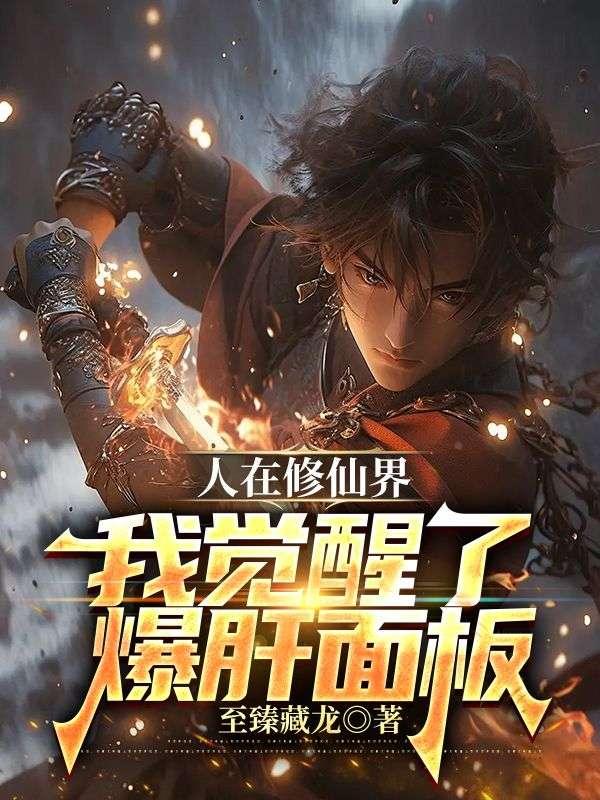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做摄政王背后的权臣狼王青竹酒百度 > 第78章(第1页)
第78章(第1页)
火炮第二日就被阎妄川着人拉走了,也好给武械处腾出地方来,这三门炮可算是他如今手里的底牌。
阎妄川这几日心情很好,因为他们家从来日理万机的殷大人终于知道粘着他了,这几日他从军营出来他们家殷大人都会来接他,以至于从前喜欢泡在军营中的人,现在都学会了早退。
“这儿。”
殷怀安出了马车冲着里面刚骑马出来的人招手,阎妄川转眼就看到了裹着雪狐大氅像是糯米团子的殷大人,也跟着上了马车。
殷怀安摸了一下阎妄川的手,果然冰凉一片,他将一个灌好的汤婆子塞到了他怀里:
“抱着。”
说完他又扯了一下阎妄川的衣服:
“都什么天了你就穿这么一个披风,生怕冻不死你是吧,一边贴膏药,一边挨冻,什么毛病?”
殷怀安是个比较耐北方那种干冷,不耐湿冷的人,空气湿度一大再一降温他就觉得浑身都冷飕飕,所以早早就把自己裹得像个球。
阎妄川抱着暖呼呼的汤婆子,听着数落,又抬眼看了一下那正在给他倒热茶的人,嘴角压不下来:
“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军中的光棍都想找老婆了,有老婆疼是不一样。”
殷怀安白了他一眼:
“谁是你老婆啊?”
焰亲王也是一个蹬鼻子上脸的人,凑过去一把抱住糯米团子:
“你说谁是?”
殷怀安一把捏在他腰上痒的地方,眯眼:
“你说谁是?”
阎妄川丝毫不犟嘴:
“我,我是你老婆,这年头给人当个老婆也怪不容易的,哎哟,别抓了,痒。”
殷怀安哼了一声住了手,阎妄川颠着他的手:
“这小细手还挺有劲儿。”
“滚。”
在城里的好处就是屋里可以长时间升暖炉,殷怀安进门脱了他狐毛大氅,阎妄川顺手接过来,认出这还是去年他送殷怀安那件:
“这要是在北境就好了,还能去猎白狐,这大氅都不是纯白的狐狸毛。”
他摩挲着那大氅上的杂毛有些不开心,总觉得殷怀安和他在一块儿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连个纯白狐毛大氅都没穿到。
殷怀安倒是浑不在意:
“什么纯白不纯白,暖和就是好衣服。”
他递给阎妄川一杯茶,阎妄川刚喝一口就皱起眉:
“这是姜水啊?”
“你那手和冰棍似的,我问过军医了,他说你这一年折损的太过了,到了冬天体寒怕冷,以后茶水都没了,换成姜茶。”
阎妄川皱着鼻子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难得有点儿孩子气地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