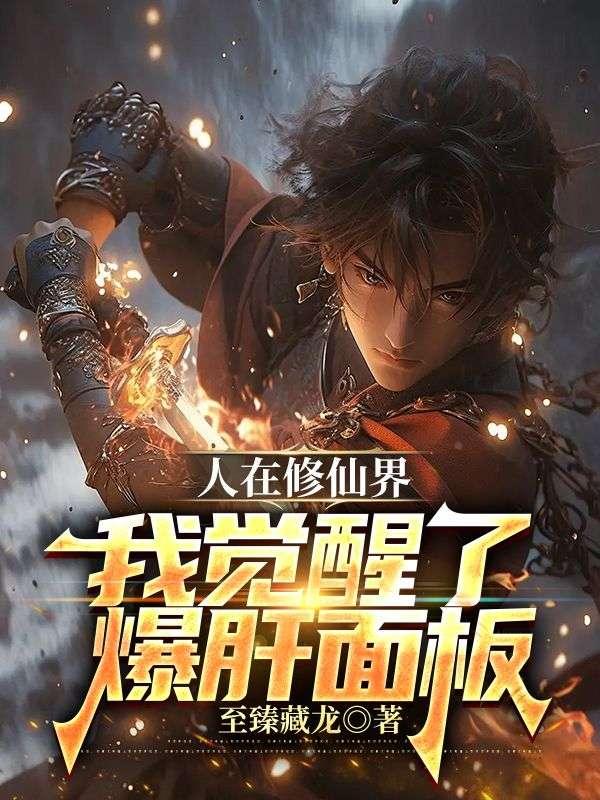看奇中文网>撒旦岛上的东方美人是什么 > 混乱(第1页)
混乱(第1页)
在圭亚那这座绿色地狱里,死亡率最高的群岛之上,蓝翅蝶、痢疾、疟疾、黄热和尸体一起组成了撒旦岛上的特产。
除了振翅的白鸥将悲告带上天堂,没有人为阿红的死亡产生一点动容。
那位鲜少出现的典狱长在半圆广场上露面时,一双双因苦役而冷漠呆滞的眼睛才有了些许恐惧。
只有刚登岛的人对典狱长没有敬畏,他们只会惊诧于第一眼的惊艳,惊艳于典狱长俊美可匹敌阿波罗神的面容。
代表了庄严和秩序的军服武装了他将近一米九的身体,高大的身形均衡而不失优雅,军帽下旁枝斜逸的金色的头发在艳阳和海风中跃动如火焰,眉骨下的一双眼睛像火中淬洗过的蓝宝石,整个人又一头冷艳的雄狮,优雅而威风。
只有庄淳月没有看到他。
枪响之后她就彻底陷入了失神,回到队伍之后更不再抬头。
阿摩利斯并不是总有兴趣莅临广场观赏死刑,他的出现属于偶然。
今日不必做礼拜,不用应付来自巴黎的电话,没有新囚犯交接,电话或电报里也没有通知暴乱发生,阿摩利斯恰好寻常得无事可做,所以他来了。
像是命中注定,他看到了一个东方女人,站在半圆广场上。
圭亚那大概也有别的东方女人,在库南、卡宴,或是圣洛朗,可他从没有注意过,也一定不是长成这样。
鹅蛋一样的脸庞和肤色,乌发像一匹华丽冰凉的黑色绸缎铺展。
她不该有一头这么漂亮的头发。阿摩利斯想。
劳作很快会消磨掉上面的光辉,让她变得跟壁炉里烧败的残灰没什么区别。
他沉默着,视线从始至终锁在那个身影上,带着儿时在米尔地区猎狐一样的专注,屏息在重重树丛之后,端着猎枪专心地观察动物的动向。
日光下,那张来自异域东方,被憔悴赋予了风情的面庞,竟值得反复琢磨。
枪响——惊飞了海鸥,白羽振翅将她的黑发扬飞在空中。
海岛艳阳融不尽她眼底静谧的冰雪,圣堂天使在奏响怦然的乐章。
女人眼瞳乌黑,有点点鲜血溅在脸上,鲜红得像痣、像雀斑,刺得人眼睛发痛。
阿摩利斯难以形容此刻的感觉。
似乎飓风终于征服绵延的海岸,刮进亚马逊雨林,将那些沉默了千百年的巨木吹出嘎吱的碎响,每一片叶子下都鼓满了风,像在挥动着手掌,汇聚在一块像刷子,将平坦的心脏扫扰得不安。
又像圭亚那结束了连绵没有尽头的雨季,等到阳光刺破厚厚云层,亲吻上这片大陆,
把整个南美洲抛入下一个季节。
收起视线,阿摩利斯默然听着神父的祷告。
直到神父走近,他向他脱帽致意:“劳烦您为有罪之人祷告。”
声音平淡得没有一点起伏,法语却在他口中变得更加华丽又充满质感。
即使到了20年代,仍有人保留着贵族后裔那份绅士礼节。
“即使罪孽再深重的人,也有聆听福音的资格。”
神父微笑地看着这位年轻人,若是在十七世纪,他一定会是令所有人骄傲的骑士,即使在当代,他也是毫无疑问的战争英雄。
只可惜不知什么原因,他并未留在巴黎领受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耀。